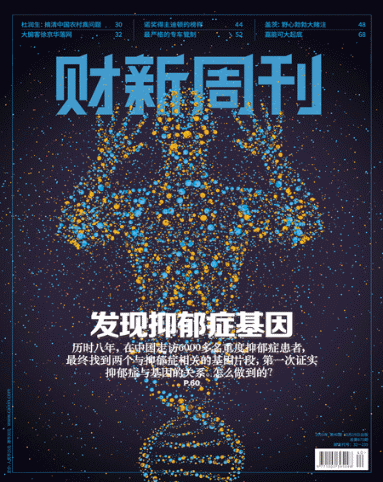
获奖人:崔筝 《财新周刊》
作品链接:http://weekly.caixin.com/2015-10-16/100863503.html
以下为作品全文:
“在你的一生中,有没有超过两周的时间,感觉到心情抑郁?”
2009年的一天,在沈阳盛京医院“CONVERGE研究”访谈室,精神科医生何强这样问来自辽宁农村的40岁女性陈芳(化名)。对于这个文绉绉的问题,陈芳有些不知所措。何强并没有过多解释,只是看着显示器,放慢语速,将这个问题又念了两遍。
花了两个多小时,陈芳才回答完所有的问题。何强将双方的问答保存归档,确认陈芳在知情书上签名;最后,用一支棉棒在陈芳的口腔中轻轻摩擦后保存。全部工作到此结束。
2007年至2012年,从深圳到沈阳,从上海到兰州,共有1万多名中国女性接受了这样的一对一访谈。她们年龄在30岁至60岁之间,汉族,坐在经过精心布置的小房间里,面对一位精神科医生,一台电脑,回答关于“抑郁”的问题。
沾有她们唾液样本的棉棒,被小心打包送至位于深圳的华大基因,进行DNA全基因组测序。她们的生命密码在测序机器上展开,化为一串串A、T、C、G,进入超级计算机,进行复杂的数据分析……
八年之后,2015年7月16日,《自然》杂志发表研究论文,首次报告两个与抑郁症相关的基因片段。这是科学界第一次证实抑郁症与基因的关系。在此之前,对于能否发现抑郁症的基因变异,科学界辩论了近百年。这篇论文给持续多年的争论画上了句号,为抑郁症的基因研究提供了明确的道路。
这篇论文的署名为“CONVERGE 研究团队”。CONVERGE既有“汇聚”之意,也是“中国-牛津-弗吉尼亚联邦大学-实验性基因流行病学研究”(China Oxford and VCU Experimental Research on Genetic Epidemiology)的缩写。
CONVERGE是英国的牛津大学、美国弗吉尼亚联邦大学(VCU)合作领导的一项研究,目的是寻找与重度抑郁症有关的基因与环境风险。团队中包括59家中国精神专科医院,或是综合医院的精神医学科,所覆盖服务的人口量几乎等同于整个欧洲的人口。
在这59家医院服务的地区,CONVERGE研究在前去医院就诊的患者中挑选6000多名重度女性抑郁症患者,以及相应数量的对照组成员进行研究。历经八年,这项研究终于达成初步重要成果。
抑郁症是最常见的精神疾病之一。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统计,全世界抑郁症发病率约为11%,全球共有超过3.5亿抑郁症患者。
抑郁症病程可长可短,可能只发作一次,持续几个月,也可能反复发作,影响一生。长期的中度或重度抑郁症属严重疾病,影响患者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最严重时,抑郁症可导致自杀。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每年自杀死亡人数高达80万人,相当大一部分自杀者患有抑郁症。预计到2020年,抑郁症将成为全球第二大致残因素。
2014年05月11日,福建省福州医学心理咨询中心,一名抑郁症患难患者在走廊等待。柳涛/CFP
抑郁症如此普遍而严重,相应的治疗方法和效果却非常有限。因此,基础研究的需求非常迫切。一个世纪以来,科学家对抑郁症的本质与病因的理解在不断加深,遗憾的是,目前人类依然无法充分理解它的许多方面。
八年研究中,数十位中国精神科医生以及深圳华大基因深度参与了CONVERGE的数据采集及分析。他们的工作帮助推进了国际科学界对于抑郁症本质的认识,还从多个角度呈现了中国本土抑郁症问题的现状和特征。
为什么选择中国?
尽管盼望了好几年,当基因数据分析的结果出来时,乔纳森•弗林特(Jonathan Flint)还是又惊又喜。寻找抑郁症的基因的过程,恰如数个团队在茫茫黑夜中赛跑,CONVERGE团队选对了路径,率先到达终点,赢得了第一轮比赛的胜利。
在过去的八年间,弗林特带领的Converge研究团队发现了与抑郁症相关的两段基因序列,并在另外3000个抑郁症病例和对照组试验中得到证实。其中一段基因用于编码一种酶,这种酶的功用目前不完全清楚;另一段基因则在SIRT1基因旁边,后者与人体细胞中负责产生能量的线粒体关系密切。这一发现,也与此前的研究相互印证。之前就有研究指出,抑郁症或许与线粒体异常相关,这是抑郁症患者为何感到疲劳和兴趣丧失的原因。
虽然这项发现离临床治疗尚有很长一段路,但或许会帮助抑郁症新药的研发,以及对患者做出更精准的诊断。
人为什么会得抑郁症?这个问题医学至今未能解释清楚。
解剖学研究发现,抑郁症患者大脑中有一些关键物质,如单胺类脑神经递质,其水平比正常人低。一则最新的发现则指出,抑郁症患者大脑海马体的某种蛋白质水平较高。这些发现,给抑郁症的治疗提供了理论依据。
目前,治疗抑郁症主要靠抗抑郁药物。但由于并不知道最终的致病因素,没有哪一种药物有把握彻底治愈抑郁症。
通过对大量患者和正常人的全基因组进行对比研究,找出与某项疾病相关的基因异变,这样的方法已经在一些疾病的研究中成功应用。但是,抑郁症的基因学研究开展非常困难。这是因为,抑郁症有诸多亚型,且发病还与环境影响因素相关,基因研究障碍重重。
此前国外科学家对同卵及异卵双胞胎的临床研究已经证实,抑郁症确实有一定的遗传性,对遗传率最高的估计约为40%。但究竟是否能够准确找到引发抑郁症的基因,科学界已争论多年。
2015年7月1日,深圳盐田北山工业区,华大基因研究院,样品与文库制备区,实验员摆放潜孔板。刘有志/CFP
像许多科学前沿问题一样,抑郁症的基因研究也是一场多国科学家团队的竞跑。弗林特的团队第一个碰到终点线,其他的研究或是进展缓慢,或是已经宣告失败。
除了CONVERGE团队,至少还有两个科学家团队已经完成或正在进行大规模样本的基因研究。此前,有研究收集了9000名重度抑郁症患者的样本,最终一无所获;另一个研究团队“Psychiatric Genomics Consortium”更是将研究的样本量扩大到了1.7万个研究对象,最终也没有任何收获。
在接受《自然》采访时,其中一个尝试失败研究团队的成员、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道格拉斯•莱文森(Douglas Levinson)高度赞扬了弗林特设计的研究方法。他认为,这或许是CONVERGE收获成功的关键,该研究方法给整个科学界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启示。
“中国是这项研究的关键。”58岁的弗林特身材瘦削、头发花白,他曾是在门诊一线工作的精神科医生,后来转向针对精神疾病的基础研究,目前在牛津大学研究、授课。他与CONVERGE研究的另一位带头人——弗吉尼亚联邦大学教授肯尼斯•坎德勒(Kenneth Kendler)同为资深的精神疾病专家,他们之前的许多研究都被认为是这个领域的经典之作。
弗林特对财新记者表示,当他设计CONVERGE研究的蓝图时,就认定这个研究只可能在中国进行。
首先,找到数千位研究对象进行访谈并不容易。弗林特表示,中国人口众多,具备大样本医疗研究的天然优势。此外,中国医疗系统完备,医生的训练良好,抑郁症的诊断、治疗也积累了一些经验,满足研究开展的基本要求。
其次,除了患者多,中国还有一些特殊的“优势”——抑郁症在中国通常诊断不足,因而被确诊的病例通常有较严重的症状,作为研究对象更具典型性。
再者,中国能够提供基因背景相似的研究对象。要大规模分析和比较抑郁症患者和正常人基因中,就要求所有受试者的背景比较相似。在美国这样的移民国家,不同种族之间通婚的历史很久,居民的基因背景非常多样。而在汉族人口占多数的中国,更容易找到基因背景相似的人群。
此外,由于抑郁症对于男性和女性的影响方式不同,且女性发病率较高,CONVERGE的研究只选女性为研究对象。
最终,对入组对象确定了诸多苛刻要求,每条都会筛去一批影响因素,让研究对象的背景更加整齐划一。CONVERGE的研究对象必须是中国女性,年龄在30岁-60岁之间,汉族,并且父母和四位祖父母都是中国汉族人;其中,患者组的成员必须被诊断为重度抑郁,第一次发病在成年之后,病程反复发作,排除双向情感障碍和任何其他精神病史,抑郁发作之前没有药物或酒精滥用问题,研究对象之间没有血缘关系。
对照组中的研究对象,则从综合医院进行外科小手术的患者以及居民社区招募,她们必须从未出现过抑郁症或其他精神疾病的症状。
研究开展
2007年,CONVERGE研究正式拉开帷幕,弗林特与坎德勒也第一次来到中国。
“那时,除了我在牛津的中国同事和学生,我一个中国人都不认识,一句中国话都不会说。”弗林特表示,以后的八年中,他每隔两三个月就来一次中国,现在已经会说不少中文,还会用汉字发简单的短信和邮件。
CONVERGE研究的第一项任务,是培训访谈员。接受培训的多为各医院的年轻精神科医生,或即将成为医生的精神卫生专业的研究生。当年在复旦读博士的杨福中,是最早参加项目的访谈员之一,如今他已经成了主治医生,在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开门诊。
随着研究推进,更多医院参与进来。2009年,何强所在的沈阳盛京医院也参与到合作单位中。与此同时,更多的二三线城市医院陆续加入。最终,参加研究的59家医院中,既有北京安定医院、上海华山医院这样的著名医院,也有江苏镇江、辽宁鞍山等地的规模较小的精神专科医院。
接下来,就是找研究对象。
一篇于2009年发表于医学期刊《柳叶刀》上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中国抑郁症患病率为6.1%。据此推算,中国抑郁症患者超过9000万人。
这9000万患者中,真正能走进医院、接受治疗的并不多。镇江精神卫生中心的主任医师张震告诉财新记者,近五年中,中国人对精神疾病的了解越来越多,尤其是城市居民,不再对抑郁症这样的问题讳莫如深。然而,城区以外的情况仍然不乐观,张震所在医院接诊的偏远郊区和农村地区的病人,几乎都是在出现准自杀行为之后,才被身边人发现异常。
“很多患者割腕后,才被家人送来看精神科。”张震从事精神科临床30多年,他表示,中国绝大部分地区的三级保健系统缺乏精神疾病防治的环节,乡镇卫生院几乎不可能配精神科医生。因此,许多抑郁症患者最初出现“不爱干活、不爱说话”的现象时,没人会意识到他们是生病了。
虽然就诊率不高,中国的精神科医生的数量也并不宽裕。各大医院的精神科常年爆满,许多名医的门诊一号难求。这客观上给CONVERGE研究带来了“便利”:不需要广撒网,最严重的抑郁症病人,在各大医院可以很容易找到。
“首先在精神科门诊调阅病历,如果一个患者的疾病情况、初步诊断符合入组的要求,我们就会和她以及她的医生联系,问她愿不愿意参与研究。”杨福中告诉财新记者,找到合适的研究对象并不容易。
“当时我们科每天会有60个-80个挂号病人,但符合入组条件的就一两个。”何强说。经过训练的访谈员会劝说她们加入研究,并约好时间,请到访谈室,搜集其DNA样本,以及症状、病史相关的消息。
项目开始初期,团队领导者会在医院坐镇监督,所有的谈话都会录音,团队的几个核心成员会定期审核他们的工作,指出不足或错误。弗林特和坎德勒分头行动,几乎走遍了所有参与项目的医院。他们需要确保每一个访谈员理解研究的意义和方法,并严格按说明执行。
访谈内容分几个部分,为保证研究的一致性,每个访谈员都必须按照屏幕上的问题一字不差地念。病人的理解能力决定了访谈的难易度。
“最难访谈的是发病期的重度抑郁症患者,她们语言迟滞、思维迟缓,对外界反应很差,要反复念问题才能听得懂。我们的要求是:如果严格按照问卷问题来念,两遍以后还没听懂,才可以适当解释一下。”何强说,有些时候,患者会跑题谈自己的其他问题,访谈员还要注意将其引导回来。
访谈内容事无巨细。除了年龄、学历这样的基本信息,还包括详细的精神病史,此外还会问到她们的个人经历,特殊事件,和父母的关系,童年时接受的养育方式等。
每个患者的访谈时间平均为两个小时。杨福中表示,在精神科门诊中,对一个病人的初诊平均时间大概是15分钟-20分钟,很少能有如此深入的交流。COVERGE的访谈系统由牛津和弗吉尼亚联邦大学合作编制,涉及重度抑郁,以及广泛性焦虑障碍、惊恐障碍等多种心理障碍进行评估,同时详细地询问并评定研究对象经历的生活压力事件、抑郁症家族史、父母亲情关系等。
在CONVERGE的访谈中,通过一层层深入的详细问题列表,许多患者从未被触及的一些情况逐渐显现出来。
“有一个患者在访谈中回答了她小时候被性侵的经历。”杨福中提及一个他印象非常深刻的病例,“在访谈结束之后,她忽然流泪了,说这件事至今为止从来没有和任何人说过,包括她的亲人、丈夫,之前的精神科和心理医生。”
在五年里,上海精神卫生中心收集了500多个病例和相应数量的对照组对象,这意味着访谈阶段投入了超过2000个小时的医生工作时间,还未加上前期的培训和后续研究。
“最重要的工作都是这些一线中国医生做的。”弗林特评论说,他们在忙碌的问诊工作中抽出时间来进行科研,并没有获得更多的报酬。
除了数十家中国医院的贡献,深圳华大基因承担了所有的DNA样本的全基因组测序工作,并从浩如瀚海的数据中,最终分析出与抑郁症相关的两段基因。北京协和医学院教授许琪另外提供了独立的3000个DNA样本。测序结果表明,CONVERGE项目组的发现在这些样本中能够重现。
这意味着,人类终于找到了抑郁症基因。
抑郁症中国特征
除了发现抑郁症基因,参加CONVERGE研究的中国医生们另有丰硕的学术收获——研究获得大量数据。这几乎是中国第一次对抑郁症人群进行如此大规模的调查。女性样本虽有一定局限性,良好的数据质量已经足够进行许多研究。
弗林特表示,CONVERGE项目经费有限,并不能给参与的医生提供丰厚的报酬,于是他想到了更好的回报他们的方式。在培训访谈医生的同时,弗林特和坎德勒面向所有参与研究的医生,开展了科学写作培训项目,“手把手”教他们怎样写英文学术论文。
最终,除了揭示抑郁症基因的《自然》杂志论文,CONVERGE的成员在国际学术期刊上一共发表了25篇学术论文,全面展现了中国女性患者抑郁症的现状特征,填补了相关的研究空白。
“这些论文最重要的发现就是,中国的抑郁症情况与世界其他国家并无不同。在中国,重度抑郁症患者的主要特征和其他国家患者是一样的。”弗林特说,此前有观点认为,不同国家的文化传统、经济状况或许会影响精神疾病的模式,但研究显示,中国的抑郁症患者的发病模式、症状、风险因素、发病人群结构等都与欧美等发达国家进行过的研究大致印证。
例如,在一系列子课题中,研究人员在中国的抑郁症患者中发现了如下特征:
重度抑郁症患者大都合并一种或多种精神障碍,例如焦虑症、恐惧症等;
童年时期的悲惨经历,如性虐待、身体虐待、遭抛弃冷落等经历,也会显著提高抑郁症的风险;
父母的养育方式亦对子女一生影响深远,父母管教方式越缺少温暖、越专制,子女患重度抑郁的风险会越高;
在患者的人生经历中,经历的压力事件越多、越严重,患病风险就更高,症状严重程度也随之上升;
抑郁症首次发病的时间亦和病情有关。患者首次发病的时间越早,发病的时间会相应越长,反复发作,并出现合并其他精神障碍的可能性越高;
抑郁症患者发病越早,走入婚姻成立家庭的可能性越低。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曾有西方学者研究认为,中国有关照产妇的文化,因而产后抑郁的几率较低。而CONVERGE研究中针对中国女性产后抑郁的研究发现,在中国产后妇女抑郁的风险因子并不比西方少。
以上的所有特征,西方的经典抑郁症研究中都曾提出相似的结论。这表明,作为一种生理疾病,抑郁症的基本特征和对患者的影响,并不随着国籍、民族、文化的不同而有明显差异。所有的抑郁症患者,都有相似的痛苦抗争。
在一些小细节上,CONVERGE研究则揭示出了一些有趣的现象。这说明抑郁症在中国确实有几点特殊。
例如,在欧洲和美国的流行病学调查都显示,低教育水平的人群患重度抑郁的风险更高,抑郁症的症状也更加严重。然而,教育水平和抑郁症风险之间的关系,在中国呈现了相反的趋势,即受教育年限越高,得抑郁症的风险越高。这个发现让研究团队惊讶不已。
研究还发现,在中国,低教育水平的抑郁症患者更易出现植物性神经症状,并且会有更多的自杀念头和计划。高教育水平患者的症状,更多表现为嗜睡、兴趣丧失等。
父母养育对孩子的影响,东西方之间也有略微不同。父母的过度保护意识,在西方通常会增加子女患抑郁症的风险,然而这部分风险因素,在中国呈现相反的效果,尤其是来自父亲的保护意识,会降低子女的抑郁风险。
这些论文陆续发表在较有影响力的国际期刊上,几乎每一篇论文的第一作者,都是参与项目的年轻精神科医生。
“虽然有一些功利,但发表论文是最实在的好处。”一位参与研究的医生说,“在参加这些项目之前,有些基层医生从未在国际刊物上发表过文章。”
在中国的医院、学术机构,论文发表量是职称、提拔的必要条件,这些论文的发表让他们受益匪浅。
在“中国知网”上搜索中文学术期刊,近几年每年都有近万篇关于抑郁症的研究论文,多为医院开展的小规模临床统计研究,更有不少“创新”研究,例如治疗抑郁症的方法就有中药“八味解郁汤”“疏肝调神针灸法”“耳豆压穴法”等。
“如果说CONVERGE项目是大学水平,国内的许多同类研究只能说是幼儿园水平。”何强不无遗憾地表示。他曾参加过国内著名医院领衔的数个大规模课题研究,最终没有实质发现,不了了之。这些研究从实验设计水平,人员投入的认真程度,和国际学术研究差距都太大。
“大家心思都不在学术上面,基层精神科医生收入少,但好在不会治死人,医患纠纷少。”何强通过越洋电话向财新记者抱怨,作为CONVERGE项目的优秀访谈员,他获得去牛津大学短期进修的机会。之后,他再三思量,决定辞职脱离体制,赴日本深造。
在CONVERGE项目在中国遭遇严重困难的时候,何强曾劝弗林特把研究移到人群基因结构相似的日本去做。但弗林特还是觉得,中国才是他的福地。
经历波折
“我刚谈妥和北京大学的合作,很快将继续进行下阶段的研究。”今年8月底,弗林特一边拿起筷子夹菜,一边高兴地对财新记者说。在关键成果发表之后,他再一次造访北京,不为庆祝阶段性胜利,而是开始运作下一阶段研究的事项。
找到两段基因只是一个开始。CONVERGE团队认为,通过采集更大样本的患者信息,能够进一步发现更多目标基因片段。弗林特介绍,他们将进一步把入组研究对象的人数扩大到3万人,患者与对照组各1.5万人。
招募难度可想而知。在第一阶段的研究中,招募研究对象并不是研究中最难的事情,中国的人口资源让这里的研究条件得天独厚。弗林特说,在中国开展研究最大的挑战,则是那些“看不见”的障碍。
“说服医院和我们合作很不容易。”弗林特觉得,一开始很多人对他们有成见,认为外国人来到中国就是来索取数据,并不会对本地做出什么贡献。“我和坎德勒花了很多时间试图改变这个观念,希望能够做出一个国际合作的范例,证明中国与国外合作的重要性。”
更有甚者,CONVERGE项目的外国背景以及大规模的基因采集活动,甚至一度引起了一些部门的警惕。许多医院避嫌退出,项目因此停滞了很长时间。
直到今天,弗林特仍然不完全明白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他只得重新找合作伙伴,并且更加努力地学习中文,以试图理解为什么自己成了“别有用心的人”。
“在我看来,这就是一个再单纯不过的科学项目。”何强介绍,所有的基因样本由中国医生采集,在华大基因进行分析,甚至从未离开中国。给中方带来影响的也只有好处:CONVERGE研究发现的抑郁症基因造福人类,中国团队的子课题研究,也让医学界对中国本土抑郁症的情况有了新的认 识。
“科学是无国界的。”张震也表示,医生们也很期待中国本土的科研力量利用得天独厚的条件开展基础研究,遗憾的是,中国的卫生部门和科研机构,已经很久没有开展针对精神疾病的大规模全国性调查研究。
最终,弗林特渡过了难关。有关部门的调查结论证实,CONVERGE确实是单纯的科学研究,在论文发表后,所有关键数据完全公开,供学界同行查阅。
经历了这一切,弗林特意识到,要想让研究在中国顺利进行,埋头做学问是不够的。
“要开展工作,需要花很多时间搞人际关系,要吃好多饭、喝很多白酒才能做成。”弗林特说。
八年下来,他逐渐学会了在中国做事情的方法,有些是他之前完全不能理解的。“例如,中国高层领导的访问团最近访问英国时会去牛津大学,我打算请求牛津的领导到时候安排我去参加会见。”弗林特耸了耸肩,“搞定了最大的老板,就没有任何阻碍了。”
据悉,中国科技部已经批准了CONVERGE下一阶段的研究。项目组将在中国更多的医院,招募更多的患者,继续攻克难题,发现抑郁之源。
时间回到2009年。在取完DNA样本之后,何强结束了对陈芳的访谈工作。他让她稍坐一会儿,写下了一份详细的诊断分析,包括她的病史、用药史,以及在访谈中发现的合并精神障碍等。
CONVERGE项目组并没有要求,这只是何强的个人习惯,对于每一个经他访谈的患者,他都给对方提供了一份详细的诊断报告。
“我认为,这是我个人对她们的感谢方式,一份微小的回报。”普通的精神科门诊不可能记下如此详尽的病历,而这样一份资料,对她们的将来的复诊、求医会有很大作用。
何强说,“她们为科学做出了贡献,却很可能无法等到CONVERGE研究真正发挥作用、抑郁症可以被治愈的那一天。”
第一批参与研究的6000多名患者的个人信息并没有出现在任何出版物中,她们中有自杀未遂的农妇,有产后抑郁的年轻母亲,有绝望的女大学生,有失去工作能力的职场白领……她们走出访谈室,继续面对与病魔抗争的人生。
“但我会记着她们。”弗林特说,“她们才是我们所有努力工作的原因。”
相关文章
- 2015年科普类优秀奖------《憨豆为何也会得
- 2015年科普类优秀奖------《比149人遇难更
- 2015年科普类优秀奖------《自闭是一种生活
- 2015年科普类优秀奖------《哈利波特的抑郁
- 2015年科普类优秀奖------《抑郁....创业者
- 2015年新闻类优秀奖------《谁来帮助社会边
- 2015年新闻类优秀奖------《精神卫生法第一
- 2015年新闻类优秀奖------《小毛病也是精神
- 2015年新闻类优秀奖------《“非正常死亡”
- 2015年创新类优秀奖------“记忆看见我”心
- 2015年创新类优秀奖------微电影《Doctor S
- 2015年创新类优秀奖------电影《等你醒来》
- 2015年创新类优秀奖------从抑郁症到马拉松
- 2015年创新类优秀奖------《走过抑郁的日子
- 2015年年度影响力金奖------“心晴 至美”
- 2015年科普类一等奖------《渡过:抑郁症治
- 2015年新闻类一等奖------《无处安放的人》
- 2015年创新类一等奖------心理脱口秀《听青


